|
编者按:在接触曾剑之前,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:拍摄时会因地制宜,迅速捕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,剪辑无师自通,凭自己的一手绝活拿了金马奖的最佳剪辑……然而站在我们面前的他,却是一个单薄、腼腆、对女友一脸温柔的小男人。李玉导演给了这个好朋友兼好男人是一个“扛上摄影机之后,整个人都会发光”的评价,无论是面对媒体和闪光灯时的腼腆,还是面对女友的柔情,无论是他的摄影才赋,还是他的剪辑天分,曾剑的多面性好像在他身上构筑了一个上不封顶的螺旋,可以助他在事业的轨道上渐行渐高,渐行渐远。
个人简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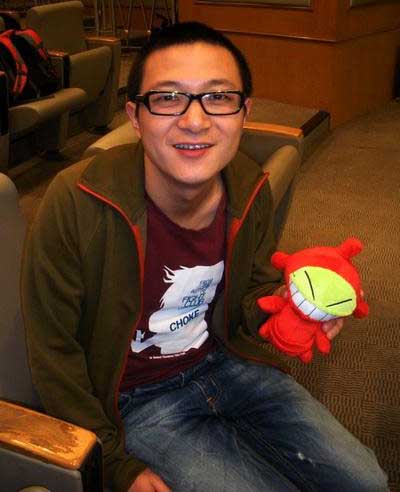
《观音山》摄影、剪辑 曾剑
曾剑,中国年轻一代的新锐摄影师及剪辑师,曾为娄烨的代表作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担任摄影、剪辑,并以此片荣获第47届金马奖最佳剪辑奖。在李玉新作《观音山》中,曾剑再次兼任摄影师及剪辑师,用他天分俱佳的视角和手法,为观众打造了一部肆意而难忘的无敌青春大戏。
左手摄影:我拍《观音山》
直觉第一 用摄影表现气质
我习惯在一拿到剧本的时候就做一个挺全的规划工作,每场戏我会想想下大概的空间是什么样的,再想象一下他们的表演大概会是什么样的,这场戏中哪些位置有哪些位置也许会有很突出的内容,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让他突出等等。看剧本的同时我也会和导演一起看一些同类电影,或老一些视觉上的图片做参考,一有空的时候就会琢磨它。

《观音山》扒火车
《观音山》这部戏是拍给70后和80后看的故事,这个故事它有它自己独特的气质,而我只是负责把它的这种气质给展现出来。看剧本的同时,我也会自己记一些东西,等拍摄的时候拿出来看看,看现场的情况和之前想的有什么不一样,或者拍摄前一晚上会拿剧本出来对比下,看是不是有前期没来及准备的东西,或者需不需要增加一些特殊的效果等等。

《观音山》火车拍摄
我在拍摄的时候,倒是没怎么注意过色彩,都是用自己的第一直觉来拍。演员会怎样演,导演要怎样调度,我尽量都不去听,只让自己用直觉来抓,这有点像纪录片的拍摄方式。
先做朋友后做事 主创间实现无障碍沟通
我以前拍过一些纪录片,跟拍纪录片出身的李玉导演很早就认识了。她对于电影这种表现形式的自由呈现感是非常好的,这一点我很认可。要说导演她有哪些地方不太好的话,大概就是她的脾气了,她是个急性子,我就很慢性子。不过一般她也还好,总的来说我们这次的合作还是挺顺利的。
我们之间的沟通并不是说只有工作的时候才会沟通,平时我们就是好朋友,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,经常扎堆一起呆着。拍戏现场的时候我们的沟通反而会比较少,但因为平时大家都太了解彼此了,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,要做什么。有需要沟通的我们会在开拍之前就把准备工作做足,现场的时间主要会留给导演和演员之间的互动,跟摄影的必要沟通会集中在开拍之前,这样安排下来整个进度会更快一些。
抓拍无限 给演员最大的表现空间
要想拍出演员最好的状态没有捷径,只能不断地拍。演员一般都会有他自己的表现习惯,拍一个礼拜左右就能对他的习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,差不多就能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感觉,凭着直觉跟过去,一般都能得到想要的镜头,主要还是要对演员有一个大概的了解。
其实在拍摄现场,我跟李玉的概念是一样的,我们都会给演员最大的自由。有时演员会问我灯的位置,具体的光位在哪儿,我就跟他们说没事儿,你们不用管我,随意的表演就行。因为有的表演,你给他一个限定告诉他从这儿到那儿,地上给他贴一个标,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很大的限制,他可能走起位来会一直盯着那个地标,这种表演太可怕了,导演和我都不大受得了这种。所以我经常跟演员说,你们只要按照自己的感觉去演,我会跟着你们的。真走到光不太好的地方,我才会跟他们说。

《观音山》剧照
独创车轮战:谈《观音山》如何赶戏
拍这片子的时候,因为编剧就是李玉和方励,沟通起来很方便,拍摄之前,随时都能改。不过也没有像有些片子的导演改得那么多的。偶尔有几次改动比较大的情况,是为了抢范冰冰的时间。那对剧组不是一般的挑战,平时一般一天可能也就拍四、五场戏,为了抢时间赶戏工作量要增加一倍,当时全组人就聚到一起开个小会,因为时间一般都会用在我们摄影这边,我就跟剧组另一个德国摄影师一起配合。我在这一场拍的同时,他去下一场景提前开始布置。等我这边弄完了大家收东西,我坐个小车先去现场,这时候他那边也差不多布置好了,我再微调一下就能用,这段时间里导演和演员们也差不多来齐了。然后我在这场拍,我那个德国同事再去下一个场景布置。就这样跟打车轮战似的一场场盯着,要不然根本抢不下来。

《观音山》剧照
《观音山》中最让摄影动情的恸哭戏
拿《观音山》中张艾嘉在车里哭那场戏来说,我觉得那场戏拍得特别好。当时她坐在她儿子出事的那辆车里,倚在她儿子摸过的方向盘上,听她儿子死前听的CD,音乐每当走到滋滋声的时候,就是她儿子死去的那个点,她就开始哭。
就这场戏,一条大概要拍5分多钟。车祸当时是有一根钢管从车窗外直接捅进来,玻璃上有那个管子捅过来的窟窿裂纹和残留的血迹。我把镜头从侧面慢慢移到窟窿那儿,拍着拍着就觉得有个角度张姐(张艾嘉)表现得特别好,我当时还在拍那个窟窿,但焦点却落在张姐那儿。我这边一直拍一边在后面打手势,镜头慢慢一点点从张姐那儿离开,到窟窿那儿,再到裂纹,沿着裂纹绕了一圈,再回到开始那个焦点,一次就拍过了。拍完后,发现张姐那儿有点收不住了,血压不太对,拍完后歇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。

《观音山》中 张姐的表现很“彪悍”
这场戏是我拍得特好的一场戏,当时真的被张姐的表演给带进去了。还有一场戏就是张姐儿子的女友来找张艾嘉,说给她儿子过生日,然后张姐就问说你过来干吗?你过来是提醒我今天既是他生日也是他忌日吗?那块也拍得挺难受的。
拍“扒火车”之前,我们先去现场采过一次景,当时大概记下了哪段隧道和哪段隧道之间拍出来比较好看,哪个隧道里面光线怎么样。真正拍的时候,火车开到那里是不会停下来的,只能是凭记忆觉得快到了,大家赶紧开始准备,一到那个景就开机。当时我们扒的那个火车是剧组包的,火车跑一圈得用一天,我们就跟着拍了一天,从早上7点到晚上5点,到头了再回来,当时还挺顺利,只跑了一趟就全部完成了。
这场戏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场面,是拍到火车上范冰冰他们三个人手拉手,演员表现得相当好。那时正好火车背向的灯打开了,但当时在火车上的我们是不知道的,只是突然觉得光线的感觉和当时气氛都挺好。拿表一量,正好够曝光,我们赶紧就把这一幕给拍下来了。
这场戏里还有一些远景的镜头,就是从远处看到范冰冰他们小小的三个人随着火车进到一个隧道里。当时我们用了两套机器,除了火车上我们这组拍近景之外,另一个摄影就爬到隧道外一个桥上俯拍整个火车的全景。
因为当时全组除了这个摄影之外大家都在火车上,为了防止拍到穿帮镜头,剧组的人用大幕布把除了演员之外的人都蒙上,等桥上的摄影摆好位,两边不停地用对讲机矫正火车通过镜头的时间,当时还挺顺利,火车一过他们就说成了,之后他们拍完就回宾馆了,我们这头火车也不停,继续拍下面的戏。
拍这场戏的时候,大家都很兴奋。除了拍远景的摄影之外,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过了一回扒火车的瘾。那天我们一共拍了四十本胶片,应该特别累的。但那天下火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觉得累,都还在那儿蹦蹦跳跳,第二天照工作不误。
《观音山》经典镜头之人工瀑布
拍瀑布那场戏的时候,我们只有一台摄影机,因为另外一个摄影是外国人,拍瀑布那个地方是国家的一个军方基站,跟国家武器有关系,不让外国人进去。所以当时就只有我一个人带着一台机器进去拍,同时山上山下各个点上都有人来配合,方励就负责总调度。但当时还有一个不太好控制的地方就是,拍瀑布之前,要先蓄满水库的水,可这个不是剧组能控制的,为了拍到更大更好看的瀑布,我们在那儿干等了两个多小时才拍上。

《观音山》人工瀑布的拍摄很惊心动魄
当时还有一个难题,就是光线。拍瀑布的那个山是个一线天的地形,光线很暗,我们的灯又进不来,一开始我们预计也就等半个小时就可以拍了,但结果等了2个小时才能拍,这时候光孔已经不够用了,就又扩充了一些,好在拍出来的效果并没有什么问题。
数字可以取代胶片 但机器永远不会取代人
虽然胶片颜色比较正,扩张感也会比较好,但现在很多摄影师都不怎么用胶片了。数字机完全取代胶片机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我自己现在也是用数字机比较多,有时也会用胶片。数字机有很多智能化的功能,可以帮助摄影师去矫正一些技术上的问题,可以省去摄影师去微调细节的时间,但再智能的摄影机我觉得也不会完全取代摄影师,毕竟机器再能干,控制机器运作的都是人,人才是拍摄过程中最主要的元素。
右手剪辑:半张剪辑人生
我在电影学院学的是摄影,但上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剪辑,有时候也会自己剪作业,没想到毕业之后还真用上了。其实这次金马奖,我是很想拿摄影的奖的,但没想到最后得到的是剪辑的奖,也挺意外的。
难以取舍:我剪《观音山》
对一个剪辑师而言,有时候自己拍的东西,自己来剪就会比较顺手。另外,也有不太好的地方,就像这次做《观音山》,拍完后我和另一位国外的剪辑师花了三到四个月的时间来做剪辑。有时候可能镜头拍得很好,但表演却没那么好,同时身为摄影和剪辑,有时就会很难取舍。拿扒火车的镜头来举例,考虑到影片的时长和故事情节的连贯性,剪辑的时候只能选最好最好的,很多很好的镜头就只能裁掉了。
因为《观音山》是一场戏一个镜头拍完的,本身并没有很严格的分镜。所以在剪辑时,我是把拍摄时自己感觉最好的瞬间全部拿出来,不管接的上或者接不上的,全部都码上,反复去看。有时看着看着,也许就会灵光一闪,发现一些镜头之间的联系,再根据这种新联系去建立一些新逻辑,这样产生的效果也会不一样。
相辅相成 从金马奖看国际合作
我是凭娄烨的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(以下简称《春风》)获得了第47届金马奖的最佳剪辑。剪《春风》时我和国外的剪辑师配合得还算可以,因为他们和我还算比较接近,都很喜欢自由呈现的风格,并且最大限度地给演员自由,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也比较顺手。其实《观音山》还有一组剪辑,是德国人,他之前剪过娄烨的《苏州河》,李玉的《苹果》他也参与过,娄烨的《春风》里他还担任了剪辑顾问。

《观音山》剧照
剪片子的时候工作量很大,一个人看同一个片子看久了,就需要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部片子,把他的新想法糅合进来。剪《观音山》的时候,我和李玉两个人剪到两个多月的时候都快要崩溃了,之后叫来了那个德国剪辑,工作了大概十几天,最后我和李玉就挑他剪得特别好的地方保留了下来。

《观音山》海报
左右互搏术:干一行爱一行
谈国产科幻:想象力比技术更关键
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看科幻的,但在中国电影不像好莱坞的市场那么成熟,大家都在尝试不同类型的电影,科幻在国内其实完全是一个空白,其实特别需要大量的技术支持。
但反过来讲,技术是一块,最主要的还是想象力,得有好的剧本。科幻电影的要求是很高的,不仅是技术,还要让技术和想象结合得特别好才行。

观音山》剧照
对新人的建议:感觉和节奏最重要
我在拍《观音山》的时候多数是靠直觉,摄影师的直觉固然对拍摄有一些帮助,但并不是说每个摄影师都要这么拍片子。这只是一个类别,其实摄影的方式有很多种,片子的类型不同,对摄影的要求也会不同。比如大片范儿的摄影师,他们就会用很详细的分镜头来拍。我这方面就比较欠缺,也正在尝试锻炼其他的拍摄方式,去接触不一样的东西,吸收更多的东西,让我的摄影语言丰富起来,更加多样化。
其实对当下的摄影师而言,技术层面的影响可以说越来越淡化掉了,关键还是人本身的东西,一个摄影师对生活的感觉,对电影的感觉,这些都是超越技术存在的东西。
剪辑师的话,说句实在话就是多看点片子。看片子的时候别光顾故事,要把注意力放到片子的节奏和剪辑技巧上。
|